久久為功:日本足球啟示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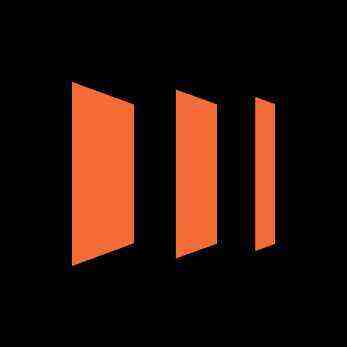
1919年1月26日,日本廣島高等師范學校操場上舉辦了三場特殊的足球賽,參賽雙方是日本的三支學生球隊和德國戰俘組成的臨時隊伍。
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德國在1914年的青島戰役中向日軍投降,4715名德軍戰俘被押往日本。為了向西方國家證明日本的現代性,日本人開展了一系列形象工程,包括組織戰俘郊游,玩臺球,踢足球也是一部分。
這批德國戰俘雖然打仗水平一般,但足球技戰術含金量極高,三場比賽灌了日本人0:5、0:8、0:6,廣島高師隊長深受震撼,每個周日都帶隊前往戰俘營學習德式足球,日德兩國在足球上的不解之緣,就此埋下伏筆。
二戰結束后,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期,隨著1964年奧運會花落日本,低下的足球水平又成了日本官員日思夜想的大事。為了能在本土奧運會上一展雄風,日本足協又一次想到了自己在二戰的盟友。
“德國人雖然發際線后退得不少,但挺直的背脊和敏銳的眼神令人印象深刻[1]。”
這是日本人見到“日本現代足球之父”克萊默教練的第一印象。
作為二戰士兵和足球運動員,克萊默的職業生涯都不太成功,因為膝傷早早退役后,克萊默跟隨德國國家隊主帥赫爾貝格走上教練生涯。在接到日本足協邀請后,赫爾貝格決定派愛徒出馬,負責對日全部事宜。
克萊默首次來到日本時,日本足球處于嚴重斷代期,眾多國腳都在戰爭中殞命,國家隊訓練還在使用土場。更落后的是日本對于足球的認知,克萊默幾乎是手把手指導日本國腳如何完成顛球、頭球,凌空抽射等技術動作。
1964年10月,在駒澤競技場的綿綿細雨中,日本隊開始了自己的奧運征程。下半場面對阿根廷2:1領先的優勢,日本隊在第36分鐘,由釜本左路傳中,日后成為日本足協主席的川淵三郎門前魚躍沖頂,將比分扳平。
這樣的頭球技術,正是來自于克萊默的傾囊相授。
克萊默指導川淵三郎頭球,1960年
1分鐘之后,又是川淵的射門被對方門將擋出,隊友跟進推射得手。日本隊以3:2戰勝了南美頭名的阿根廷,驚險闖入八強,完成了賽前的既定目標。
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在與尼日利亞、巴西與西班牙的死亡之組中,日本一勝兩平順利出線,并在1/4決賽淘汰法國。雖然在半決賽里不敵舉國體制的紅色匈牙利,但日本在三、四名決賽中2:0力克東道主墨西哥,拿到了一枚具有歷史意義的銅牌。
作為日本現代足球的啟蒙者,克萊默深知這塊銅牌背后有眾多偶然因素,日本足球從青訓梯隊到職業聯賽的體系建設還是一片空白。
在克萊默的推動下,日本足球聯賽其實早在1965年正式成立,比德國甲級聯賽只晚了兩年,但日本的問題是只有聯賽卻沒有職業化。當時的日本聯賽,只是一個由大企業內部足球隊組成的業余聯賽,性質等同于東芝索尼NEC這些公司的團建+聯誼組織,其競爭力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這些已經進入日企年功序列的全職球員,主要目標是通過球賽全力配合企業形象宣傳與建設,而無需對球迷和地方榮譽負責。指望這類球員能賽出風格賽出水平,顯然癡人說夢。
現代足球之所以誕生在英國,核心在于足球的產業化,即把足球從一項運動變成一個產業。
1885年的英國,球員作為一個職業被法律所確認,球隊成為商業機構。時至今日,比賽日收入(主要是球票)都是很多球隊主要的收入來源。由于球員工資和球隊收入開始與比賽質量掛鉤,英國聯賽質量和技戰術水平迅速提高。
后世足球后發國家的改制也證明:相比于旱澇保收的體制,職業化可以迅速調動起球員的積極性。1994年中國足球改制,第二年北京國安隊就在對抗賽中把阿森納和桑普多利亞斬于馬下,在90分鐘內逼平了上一年的歐冠冠軍AC米蘭,著名足球評論員張路感慨:
“他們打意甲,也沒有累成這個樣子,嘿嘿[6]。”
日本的職業化足球起步并不比中國早多少,1985年世界杯預選賽,“企業聯賽”體制下組成的日本隊在關鍵戰輸給老冤家韓國隊,1987年又在家門口輸給中國隊無緣奧運會。危機倒逼改革,日本上下達成共識:想救日本足球,必須推進職業化。
1988年,失意的日本足球等來了一位職業化改革的舵手人物,川淵三郎。
對于企業足球而言,對足球古道熱腸的領導,以及企業自身良好的經營背景,兩者缺一不可,廣州隊老板對此想必深表認同。
作為企業足球體制的親歷者,川淵三郎曾在古河工業的足球隊踢球,然而伴隨著高層變動,以及古河盈利的下滑,古河足球部卻在日后一度陷入到了全年被迫停賽的窘境。
1990年3月,在數十次會議之后,川淵三郎力排眾議,公布了職業聯賽加盟的“七大條件”。其中,球隊“法人化”和“根據地”成為了關鍵詞。“法人化”意味著球隊必須獨立于企業存在,而“根據地”則意圖為新球隊建構起新的生命力,使其成為根植于所在地區的現代職業俱樂部。
但川淵三郎的“七大條件”門檻過高,在同年的會議上存在著不少反對的聲音,川淵起身發表了一段即興演講:
“對于那些總是說時機沒有成熟的人來說,即使過了100年,他們也還是會說時機沒有成熟。對于那些說沒有成功先例的人來說,即使過了200年,他們也還是會說沒有成功的先例。”
1991年2月,“J聯賽創始十隊”誕生。1991年7月1日,日本職業足球聯盟官方名稱與標志正式公布,愛稱則是“J聯賽”。而在與德、英、意聯賽規章全譯對比之后,J聯賽決定以德甲為范本制訂聯賽規章。德國再次成為了日本人的老師。
1993年5月15日,東京國立競技場座無虛席,前一日的雨水洗刷讓晴好的天空顯得分外澄澈。J聯賽的開幕式在當晚7時拉開帷幕。開幕節點卡在了泡沫經濟的余韻,晚會的審美基調仍然昂揚向上,日本足球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濟科、鄧加、萊因克爾等巨星的加入,使得J聯賽早期就在球迷群體中獲得了極大成功,球隊商業化進展順利;巨星的言傳身教,對于本土球員的技戰術和職業素養,也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還有一些頂層設計的成效則是慢慢顯露的:在J聯賽開賽前,日本全國沒有一所專門的足球體育場,J聯賽開賽之后30年,日本已經建起來了二十多個能夠容納萬人以上的專業足球體育場。
川淵三郎另一個影響深遠的舉措,是強化了依托于J聯賽俱樂部的青訓體制。職業梯隊與日本原有的校園足球體系構成的“雙軌制”,進一步優化了球員的培養選拔體系與成長路徑。
本屆世界杯為日本隊打入第二個進球的淺野拓磨,在成為運動員之前一直是邊讀書邊踢球,在高中足球錦標賽上出盡風頭后被球探相中,加入職業俱樂部。
另一位“名古屋奇跡”相馬勇紀,從小就在職業俱樂部訓練,但18歲時郁郁不得志,就回去讀書考大學了。沒想到他是個大器晚成的選手,讀到大四才展現出足球天賦,入選了日本國家隊。
這套層層選拔的體系既為足球人才提供了職業化道路,又為那些踢不出來的球員提供了退路——可以回學校讀書,再出去打工。
所謂職業化,本質上是通過商業化手段讓足球俱樂部可以自我造血,讓足球運動員可以通過踢球養活自己,這樣才能做大球員基數,在高強度的競爭中篩選出最優秀的球員。
1993年世界杯預選賽,成長于改革年代的日本隊面臨第一次大考。結果在最后一輪2:1領先伊拉克的情況下,日本隊仍然大舉進攻,伊拉克通過快速反擊打入扳平進球,在日本足球史上被稱為“多哈悲劇”。
當時間來到1998年,法國在本土世界杯上大獲成功,而日本隊則沒能實現初戰世界杯“一勝、一負、一平”的目標,以三戰皆墨結束了首次征程。當時還在J聯賽執教的溫格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足球的水平絕對不低,但勝利才是最重要的[1]。”
作為4年之后韓日世界杯的東道主,日本順勢將新老師瞄準了法國,幾乎全盤吸收了法國的青訓系統。為了應戰02年世界杯,日本人直接請來了一位法國教練,特魯西埃。
這位法國人日后也曾在深圳隊執教,獨具個性的李毅大帝在此期間對其執教理念頂禮膜拜。
球員個性,是特魯西埃在日本隊強調的核心。在他看來,取勝正是源于60%的戰術,30%的個性以及10%的運氣,而日本隊球員缺乏的恰恰是自我意識。在他麾下,球員不得使用敬語。
在2000年黎巴嫩亞洲杯賽前,特魯西埃還將所有日本對球員趕出了酒店,讓他們感受陽光、海風、還有美麗的姑娘。
2002年6月世界杯小組賽上,特魯西埃的日本隊先是2:2逼平比利時,然后又以1:0和2:0干脆利落地擊敗了俄羅斯和突尼斯,順利晉級。雖然在淘汰賽中不敵土耳其,但第二次參加世界杯的日本隊就此闖入16強。時至今日,日本隊依舊徘徊16強的藩籬前。
為了尋求突破,日本隊又前后接連在此后20年間嘗試了5任外籍主帥。然而在此期間表現更為奪目的,卻是本土主帥。
日后曾深耕杭州綠城的岡田武史在2010年世界杯中,通過強調毫無保留的跑動,帶領日本隊第二次闖入了16強,只不過在點球大戰倒在了巴拉圭面前。而在2018年臨危受命的西野朗,帶著他的攻勢足球再次率隊闖入16強,如果不是最后比利時最后時刻的14秒絕殺,距離封神只差一步。
事實證明,任何一個國家想在足球王國內爭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當然可以借助他人的先進經驗;但是想要更進一步,唯有找到并踐行自己的路線。
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結束,日本足協將下一任主帥鎖定在了森保一身上。這不僅是出于對這位在J聯賽冠軍教頭的認可,也是足協對俄羅斯世界杯反思后做出的理性選擇。日本隊在比利時面前倒下正是因為防守出現了紕漏,而森保一則以善于調教防守著稱。
日本足協慷慨給予了森保一4年的準備期,而且還把國奧隊一并交到了森保一的手里。上任初期的森保一甚至將考察延伸到了大學生聯賽,如今效力于英超布萊頓的三笘熏便由森保一在大學生聯賽發掘。
而在戰術上,森保一的執教風格是在穩健的防守中找出致命機會,并且努力讓每個球員的特點最大化。比如堂安律擅長分球后向前跑位,森保一在世界杯上也利用了他的特點。世界杯上面對德國和西班牙的兩場勝利,都是堂安律的進球吹響了反擊的號角。
在克萊默來日技術扶貧60年后,日本人在世界杯上以2:1戰勝了昔日的老師。盡管還沒有突破世界杯八強的天花板,但正如森保一在1/8決賽后的感慨:
“如果你一直希望看見山對面的風景,我想你一定會翻過這座山的。”
衡量一個國家的足球人才底子厚不厚,有一個非常直接的指標:足球人口。
足球人口一般指的是在本國足協登記在冊的各級別足球運動員的數量,由于統計口徑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數據往往有一些差異,日本的足球人口大概在30萬-100萬之間;韓國則在30-50萬;軟柿子泰國大約也有20萬足球人口。
中國足協并沒有公開注冊球員統計這項數據,今年4月,國腳楊旭在一場直播里說:“中國足球注冊球員只有8000人左右,日本有50萬,越南都有5萬,連冰島總人口那么少的國家,注冊球員也有2萬。”
職業足球本質上是一種市場環境下的殘酷選拔,德法意這類足球大國,各級聯賽一線隊和梯隊球員總和往往超過15000人,但真正為輿論所關注的,往往只有頂級聯賽不過幾十名一線隊球員。
而對國家隊來說,想要選出26個能打進世界杯的球員,需要的是1000多個球員組成的頂級聯賽,10000多個球員組成的次級聯賽,超過十萬個球員組成的足球人口。需要做的不是提高塔尖的高度,而是做大金字塔最底層的厚度。
相比成績和榮譽,足球首先是一個產業,和其他產業的規律并無太多不同。
它的繁榮,依賴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的造血模式、一個足夠龐大且成熟的消費群體以及參與者系統性的成長和退出機制。顯然無論其中哪一個要素,中國足球都有著不小的距離。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啟了足球職業化道路,然而結果卻大相徑庭。
1992年6月23日,紅山口會議開啟了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序幕。在這場近乎“休克療法”的改革中,體工隊培養模式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中國足球卻沒能建構起新的造血模式。
2002年,依靠著體工隊模式余暉的中國隊與日本隊一同踏上了韓日世界杯的征程。同一屆世界杯,這是日本隊晉級世界杯16強的起點,卻也是中國足球未曾再抵達的高度。
參考資料
[1] 日本足球史,符金宇
[2] 日本足球的老師之“德國篇”系列,符金宇
[3] 特魯西埃曾接近國足主教練 "白巫師"魔法不在,新民晚報
[4] 特魯西埃直言不諱:日本其實沒有足球文化,遼沈晚報
[5] 日本人如何監督換帥,有馬體育
[6] 職業化給中國足球帶來了什么?,瞭望
[7] 日J聯賽成功20載背后 中國足球這點痛算什么,騰訊體育
編輯:李墨天
視覺設計:疏睿
責任編輯:李墨天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遠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作者:鄭鵬飛,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