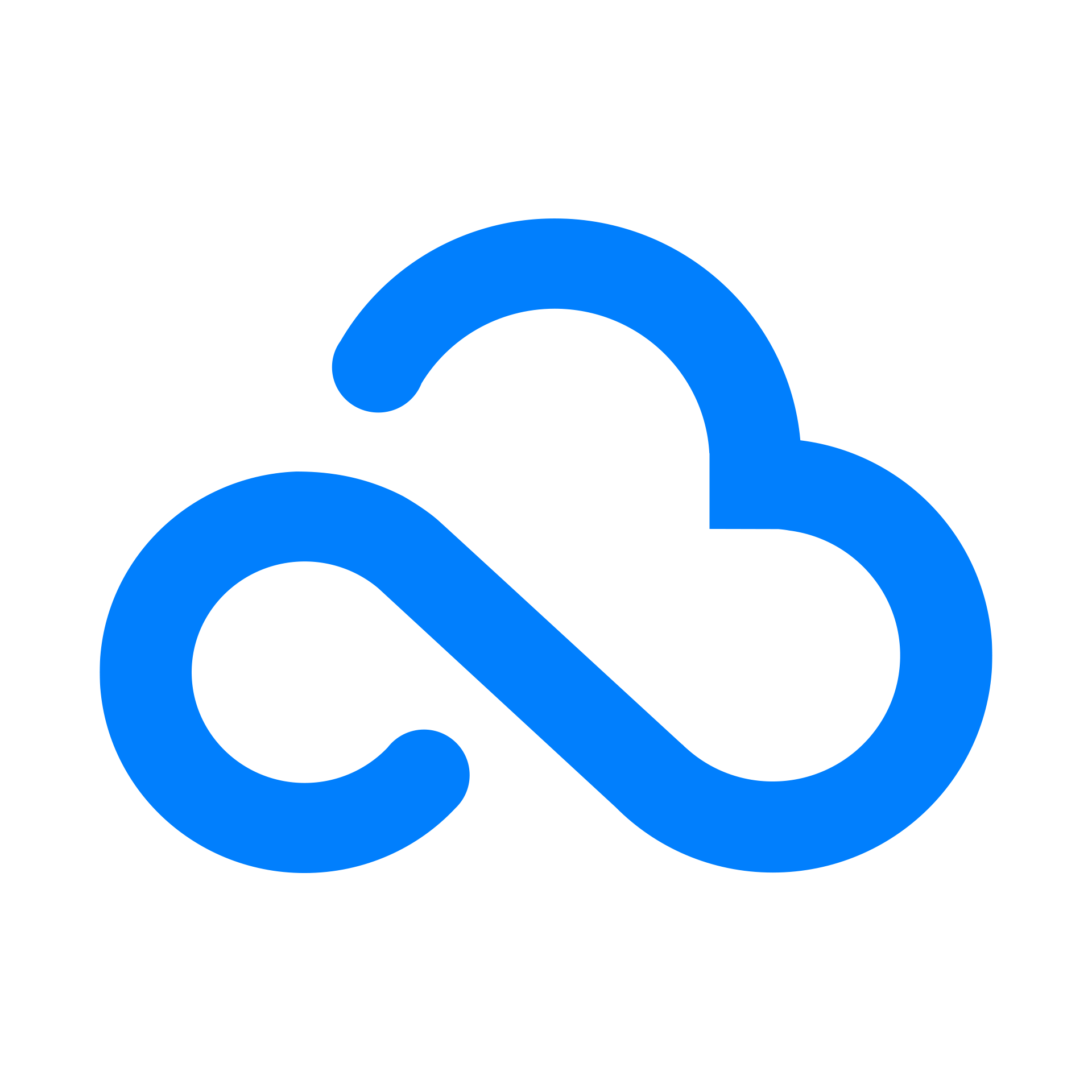以隱私的名義,一場數(shù)據(jù)的戰(zhàn)爭打響了

當(dāng)數(shù)據(jù)已經(jīng)成為新時(shí)代的石油,當(dāng)數(shù)據(jù)所有權(quán)尚未清晰,科技圈的暗戰(zhàn)已然開打。
在舊金山的「新硅谷」SOMA 區(qū),通往海灣大橋的高速公路旁,佇立著一塊鴨子廣告牌,上面寫著:「谷歌在追蹤你。我們不會(huì)。」
說這話的鴨子來自 DuckDuckGo,一家主打隱私保護(hù)的搜索引擎公司。
DuckDuckGo 在舊金山「新硅谷」SOMA 地區(qū)的廣告牌|圖片來源:WIRED
在美國,DuckDuckGo 有 2245 塊廣告牌,在歐洲是 2261 塊。這對(duì)于一家科技公司來說并不尋常。
通常,科技公司更傾向于在線上投放廣告。根據(jù)用戶數(shù)據(jù)生成的定向廣告可以讓公司更高效地找到他們的目標(biāo)用戶。DuckDuckGo 選擇了廣告牌這種老派的方式——這是為了以行動(dòng)樹立這家企業(yè)的價(jià)值觀:不追蹤用戶。
去年,DuckDuckGo 的應(yīng)用下載量超過了 5000 萬次,比之前所有年份的總和還多,年收入也相應(yīng)突破了 1 億美元(約合 6.5 億元人民幣)。要知道,這家成立于 2008 年的公司,在上一輪融資過后,估值也就 7480 萬美元(約合 4.86 億元人民幣)。看起來,它主打隱私的價(jià)值觀奏效了。
最近,DuckDuckGo 憑借 2.42% 的市占率,超越必應(yīng)、雅虎成為了美國第二的移動(dòng)搜素引擎。而第一名的谷歌,是 94.36%,DuckDuckGo 的 39 倍。
這是一個(gè)大衛(wèi)挑戰(zhàn)哥利亞的故事,但在這個(gè)故事中,「大衛(wèi)」揮舞的不是石子,而是「隱私」這桿大旗。
種種數(shù)據(jù)表明:在巨頭格局確立,新秀創(chuàng)業(yè)公司本沒有多少增長空間的當(dāng)下,以隱私為名的新一代數(shù)據(jù)之爭已經(jīng)拉開序幕。
2020 年 6 月,蘋果的隱私工程經(jīng)理凱蒂·史金納(Katie Skinner)在 WWDC(世界開發(fā)者大會(huì))上用 20 秒介紹了 iOS 14 的一個(gè)「小小更新」:App 在搜集用戶數(shù)據(jù)之前,必須征求用戶同意。一旦用戶不同意,就會(huì)關(guān)閉 IDFA 碼(Identifier For Advertisers),蘋果的廣告主標(biāo)識(shí)符。
這個(gè)搜集用戶數(shù)據(jù)的 IDFA 開關(guān),在去年 6 月之前還是默認(rèn)開啟的。但在 iOS 14 上,這成為了一個(gè)顯性的可選項(xiàng)。當(dāng)用戶第一次打開 App 時(shí),iOS 會(huì)彈窗詢問:「是否同意 App 對(duì)你進(jìn)行跨網(wǎng)站、App 的追蹤?」顯然,多數(shù)用戶并不會(huì)同意,這就直接切斷了定向廣告的數(shù)據(jù)來源。
這是蘋果應(yīng)用追蹤透明度(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ATT)的一部分。2021 年 5 月,一項(xiàng)針對(duì)美國 300 名 iPhone 用戶的調(diào)查指出,73% 的受訪者對(duì)這項(xiàng)隱私政策都表示贊同。蘋果的 CEO 蒂姆·庫克(Tim Cook)也在 2021 年第三季度的財(cái)報(bào)電話會(huì)議上回應(yīng),在 ATT 推出之后,蘋果受到了相當(dāng)積極的回饋。
「你的 App 想要追蹤你的數(shù)據(jù)給你發(fā)廣告,你同意追蹤嗎?」|圖片來源:AppleFacebook 認(rèn)為蘋果的做法扼殺了中小企業(yè),而 Facebook 將立場鮮明地與中小企業(yè)站在一起。|圖片來源:Twitter@DaveStangis
但對(duì)于所有以線上廣告為商業(yè)模式的公司來說,這可能是一場性命攸關(guān)的大震蕩。反應(yīng)最激烈的是 Facebook。2020 年 12 月,它買了下了《紐約時(shí)報(bào)》的一整個(gè)版面,公開反對(duì)蘋果。
在 Facebook 的口徑中,蘋果的做法嚴(yán)重限制了中小企業(yè)的生存。大企業(yè)有足夠的財(cái)力進(jìn)行大規(guī)模廣告投放,但中小企業(yè)如果沒有精準(zhǔn)投放技術(shù),就很難找到潛在的用戶群,廣告投放的效率會(huì)大大降低。根據(jù) Facebook 說法,這會(huì)平均降低中小企業(yè) 60% 的收入。
Facebook 認(rèn)為蘋果的做法扼殺了中小企業(yè),而 Facebook 將立場鮮明地與中小企業(yè)站在一起。|圖片來源:Twitter@DaveStangis
雖然 Facebook 的言論看起來是純粹利他的,但和大眾印象不同,表面上是一家科技公司的 Facebook 其實(shí)是一家廣告公司。2020 年四季度財(cái)報(bào)顯示,F(xiàn)acebook 的 280.7 億美元(約合 1825.84 億元人民幣)的收入中,96.8% 都來自廣告。Facebook 曾在 iOS 14 測試版上小規(guī)模測試過,結(jié)果廣告收入出現(xiàn)了 50% 的下跌。
在財(cái)報(bào)公布后的電話會(huì)議上,F(xiàn)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更是直白地說道:「蘋果嘴上說他們?cè)趲椭脩簦珜?shí)際上這件事顯然是利益驅(qū)使。」
Facebook 和蘋果的本質(zhì)矛盾在于這兩家公司商業(yè)模式的不同。廣告是 Facebook 的核心業(yè)務(wù),廣告商是它的主要客戶。但蘋果是一家電子消費(fèi)品公司,面向的是 C 端用戶,包括 iPhone、iPad、Mac 和其他可穿戴式設(shè)備的硬件銷售才是它的主要收入。
實(shí)際上,讓業(yè)界如此在意的 IDFA 就是蘋果隱私政策的產(chǎn)物。在 IDFA 問世之前,App 可以直接讀取到手機(jī)的唯一識(shí)別碼,無論是 MAC 地址、UDID 還是 UUID。IDFA 的不同之處在于用戶可以重置或者關(guān)閉這個(gè)識(shí)別碼。雖然 IDFA 的關(guān)閉入口隱藏得很深,但蘋果給了用戶一個(gè)選擇:是否要讓 App 給你推送定向廣告。需要注意的是,關(guān)閉 IDFA 并不會(huì)減少廣告數(shù)量,只是定向廣告的精度會(huì)下降。
但扎克伯格的「攻擊」不是沒有來由,蘋果并非隱私保護(hù)的「天使」。在打擊競爭對(duì)手廣告業(yè)務(wù)的同時(shí),蘋果也在擴(kuò)大自身的廣告版圖。
蘋果的廣告業(yè)務(wù)主要有兩種,App Store 的搜索廣告和新聞、股市應(yīng)用的展示廣告。目前,蘋果的搜索廣告業(yè)務(wù)(Apple Search Ads)已經(jīng)在中國上線。這項(xiàng)在 2016 年就推出的業(yè)務(wù)允許開發(fā)者以競價(jià)的方式投放廣告。
而根據(jù) FT 中文網(wǎng)的報(bào)道,蘋果正在計(jì)劃為 App Store 增加第二個(gè)廣告位。
以抖音為例,在 App Store 搜索「抖音」后,排名第一的是「快手」的廣告
事實(shí)上,蘋果一直在試圖進(jìn)入廣告業(yè)務(wù)。早在 2010 年,蘋果就推出了移動(dòng)廣告平臺(tái) iAd。在喬布斯看來,當(dāng)時(shí)的移動(dòng)廣告「實(shí)在太爛了」。他不想把 iAd 做成低俗的廣告平臺(tái),而是希望這個(gè)平臺(tái)上可以呈現(xiàn)優(yōu)雅的、不會(huì)讓用戶反感的廣告。也因此,iAd 設(shè)立了 50 萬美元的高門檻,這讓很多中小公司望而卻步。最終 iAd 于 2016 年 6 月關(guān)閉。
三年前,蘋果也自己設(shè)計(jì)了一套廣告追蹤框架——SKAdNetwork。它和 IDFA 一樣可以追蹤廣告投放的效果,但出于種種數(shù)據(jù)保護(hù)方面的限制,也很難稱得上好用。但是在眼下「嚴(yán)苛」的蘋果新政面前,SKAdNetwork 可能是廣告主們最好的選擇了。
雖然目前廣告業(yè)務(wù)只占蘋果營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對(duì)于既當(dāng)「裁判」又做「守門員」的蘋果來說,它用一套新的隱私規(guī)則,完成了「清場」。
根據(jù)投資管理公司 Alliance Bernstein 的分析師托尼·薩克納吉(Toni Sacconaghi)估計(jì),蘋果公司在 2021 財(cái)年的廣告收入將從 2017 財(cái)年的 3 億美元增加到 30 億美元左右。到 2023 或 2024 財(cái)年,蘋果廣告的年銷售額可能會(huì)增至 70 億至 100 億美元之間,這將推動(dòng)蘋果服務(wù)業(yè)務(wù)的增長高達(dá) 3 個(gè)百分點(diǎn)。
自 2011 年 iPhone4 問世以來已經(jīng)過去了 10 年,蘋果領(lǐng)先業(yè)界的硬件優(yōu)勢(shì)逐漸被各大安卓手機(jī)廠商追平,甚至超越。當(dāng)用戶需要一個(gè)「為什么非得是蘋果而不是安卓」的理由時(shí),隱私保護(hù)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
在喬布斯選擇封閉系統(tǒng)開始,就為 iOS 種下了隱私保護(hù)的基因。蘋果的隱私政策并非橫空出世,而是在逐步收緊。IDFA 的風(fēng)波切中了一個(gè)我們當(dāng)下這個(gè)時(shí)代必須回應(yīng)的問題:技術(shù)在侵犯用戶隱私嗎?
2006 年的時(shí)候,英國數(shù)學(xué)家克萊夫·漢比(Clive Humby)首次把「數(shù)據(jù)」比喻成了「新的石油」。此后,這種說法就在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學(xué)者和 CEO 的口中頻頻出現(xiàn)。
石油的珍貴在于它是不可再生的能源,但數(shù)據(jù)是可以無限產(chǎn)生和重復(fù)利用的,今天的互聯(lián)網(wǎng)上每天都在產(chǎn)生海量的數(shù)據(jù)。
這個(gè)比喻成立的邏輯在于,整個(gè) 20 世紀(jì),標(biāo)準(zhǔn)石油、荷蘭皇家殼牌、英國石油公司,這些控制著石油的公司也控制著經(jīng)濟(jì)的命脈。放在今天,是谷歌、Facebook 這些科技巨頭。
本世紀(jì)初,手握海量數(shù)據(jù)的科技巨頭們發(fā)展出了一門新生意——線上定向廣告。到 2019 年,全球網(wǎng)絡(luò)廣告的市場規(guī)模已經(jīng)突破 3000 億美元(約合 1.95 萬億元人民幣)。
在廣告業(yè)一直流傳著這么一句話:「我知道在廣告上的投資有一半是無用的,但問題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說這話的是百貨業(yè)之父約翰·沃納梅克 (John Wanamaker),那是 100 多年前,傳統(tǒng)廣告的黃金時(shí)代。
情況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發(fā)生了變化,科技的進(jìn)步讓廣告成為了一件很高效的事情。某種程度上,沃納梅克的迷思已經(jīng)不再成立,各大科技公司可以很方便地追蹤用戶行為、記錄廣告投放所獲得的下載或購買轉(zhuǎn)化次數(shù),而廣告主以此決定向各流量平臺(tái)支付多少廣告費(fèi)用。
你或許有過這樣的經(jīng)歷,在網(wǎng)頁搜索咖啡之后,就會(huì)在電商平臺(tái)發(fā)現(xiàn)咖啡相關(guān)的推薦商品,手機(jī) App 似乎在時(shí)刻監(jiān)視你的網(wǎng)絡(luò)生活。很多人甚至懷疑 App 在竊聽用戶,這在理論上可行,但實(shí)際上并不成立。
實(shí)時(shí)監(jiān)聽對(duì)話有很高的帶寬成本,巨大的流量很容易被用戶察覺,也會(huì)給公司帶來很高的存儲(chǔ)和人員壓力,是一筆不劃算的買賣。并且,僅就定向推薦而言,已經(jīng)有很成熟的技術(shù)支持,亞馬遜在二十年前就使用的鄰近算法推薦在今天依舊在廣泛運(yùn)用。
最為關(guān)鍵的是,竊聽用戶本身就是違法的,越是大公司,對(duì)數(shù)據(jù)合規(guī)就越謹(jǐn)慎。
而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做到這種近乎監(jiān)控式的廣告推送,都建立在對(duì)用戶的信息采集上。科技公司通常會(huì)搜集三類用戶數(shù)據(jù)——行為數(shù)據(jù):比如網(wǎng)頁瀏覽歷史、停留時(shí)長、使用了哪些在線服務(wù);消費(fèi)記錄:比如你購買了哪些商品、退換貨記錄;個(gè)人信息:用戶的年齡、學(xué)歷、性別、所在地區(qū)等。
這些信息在后臺(tái)就是一個(gè)個(gè)事實(shí)標(biāo)簽。通過算法,這些標(biāo)簽就形成了所謂的用戶畫像。在大公司內(nèi)部,這些數(shù)據(jù)是流通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你在谷歌搜索的商品會(huì)出現(xiàn)在 Youtube 的前插廣告中,早在 2006 年,谷歌就以 16.5 億美元(約合 107.25 億元人民幣)的價(jià)格收購了 Youtube。
除此之外,這些大公司也會(huì)為中小 App、網(wǎng)站提供相似的用戶分析服務(wù),并通過平臺(tái)聯(lián)系廣告主投放廣告,形成廣告聯(lián)盟。
這種做法最早由亞馬遜發(fā)明,時(shí)至今日,大型的科技公司幾乎都創(chuàng)建了類似的廣告聯(lián)盟,F(xiàn)acebook 的 Audience Network,谷歌的 Adsence,阿里巴巴的友盟,騰訊的廣點(diǎn)通和字節(jié)跳動(dòng)的穿山甲。
在這些公司對(duì)外的口徑中,所有的數(shù)據(jù)都是經(jīng)過脫敏處理的,所輸出的是一個(gè)群體畫像,無法從中反推出個(gè)人信息。但這些信息是如何采集的,又是如何在公司的內(nèi)部和外部流通的,對(duì)于普通用戶來說依舊是一個(gè)無法打破的黑箱。而目前也并沒有一家科技公司明確地地向用戶披露這個(gè)過程。
當(dāng)科技公司頻頻爆出數(shù)據(jù)泄漏丑聞時(shí),這種「不透明」就成為了用戶恐懼的源頭。2018 年,英國咨詢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就被爆出在未經(jīng) Facebook 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利用 5000 萬用戶數(shù)據(jù)為美國前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活動(dòng)提供幫助。
事后,有人在 Twitter 上發(fā)起了 #DeleteFacebook 的運(yùn)動(dòng),好萊塢導(dǎo)演羅素兄弟甚至以此為題材拍攝了一部電影。
「為什么我的數(shù)據(jù),成為了你牟利的工具?」這可能是絕大多數(shù) Facebook 用戶的心聲。尤其當(dāng)數(shù)據(jù)交易已經(jīng)成為一門事實(shí)上的生意時(shí),數(shù)據(jù)的歸屬權(quán),就成為了一個(gè)繞不開的問題。
等價(jià)交換是通行千年的交易準(zhǔn)則,買賣雙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完成價(jià)值交換。
而對(duì)于定向廣告而言,交易的雙方發(fā)生在公司和廣告主之間,用戶并不從中獲利。很多用戶對(duì)于信息采集的反感都來自于此:我好像失去了什么東西,但并沒有得到相應(yīng)的回報(bào),而那些科技公司卻輕松賺取了上億的利潤。
關(guān)于數(shù)據(jù)的歸屬權(quán),主流的評(píng)論大致有兩種觀點(diǎn)。
有一方觀點(diǎn)認(rèn)為數(shù)據(jù)的歸屬權(quán)應(yīng)該歸平臺(tái)所有,因?yàn)橛脩粝硎芰丝萍脊咎峁┑拿赓M(fèi)服務(wù)。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薛兆豐曾經(jīng)引用過著名的「科斯定律」。
一項(xiàng)有價(jià)值的資源,不管從一開始他的產(chǎn)權(quán)歸誰,最后這項(xiàng)資源都會(huì)流動(dòng)到最善于利用他、能最大化利用其價(jià)值的人受理區(qū)。這是科斯定律的一個(gè)重要含義。而在制度設(shè)計(jì)中,我們應(yīng)該盡量讓這種資源的流動(dòng)和分配更方便、容易,從而提高各項(xiàng)經(jīng)濟(jì)資源的使用效率。
簡單來說,薛兆豐的結(jié)論是,(資源)誰用得好,就應(yīng)該歸誰。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來說,這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市場研究公司愛德曼·博嵐(Edelman Berland)曾對(duì)全球 15 個(gè)國家的 1.5 萬名用戶展開調(diào)查:「你愿意以犧牲一些隱私為代價(jià),換取更多便利與舒適嗎?」有 51% 的受訪者表示不愿意,27% 表示愿意,剩下的受訪者沒有意見或不知道如何回答。
這揭示了一個(gè)關(guān)于隱私的悖論:公眾越來越意識(shí)到在線共享數(shù)據(jù)的風(fēng)險(xiǎn),但是,為了某種便利,人們依舊在披露自己的數(shù)據(jù)。
因?yàn)橛脩敉亲顩]有話語權(quán)的,也很難對(duì)數(shù)據(jù)使用產(chǎn)生有效的監(jiān)督。當(dāng)科技公司的產(chǎn)品已經(jīng)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基礎(chǔ)設(shè)施時(shí),用戶沒有別的選擇。舉個(gè)例子,即使你不同意微信的隱私條款,也很難不使用微信,因?yàn)槟闼械纳缃魂P(guān)系幾乎都在微信上。
另一方觀點(diǎn)認(rèn)為數(shù)據(jù)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該歸用戶所有。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的《歐盟通用保護(hù)數(shù)據(jù)條列》(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GDPR)號(hào)稱「史上最嚴(yán)格的隱私保護(hù)法」。在這部條列中,人類首次在法律層面上明確了用戶數(shù)據(jù)的所有權(quán)屬于用戶,而平臺(tái)只能管理及合理使用這些數(shù)據(jù)。
但是在我國,數(shù)據(jù)的歸屬權(quán)問題還沒有明確的結(jié)論。我國 2021 年實(shí)施的《民法典》明確了「個(gè)人信息」的定義和處理原則,必須征得個(gè)人同意才能處理個(gè)人信息,但沒有明確個(gè)人信息的歸屬權(quán)。而 2017 年生效的《網(wǎng)絡(luò)安全法》,包括正在審議的《數(shù)據(jù)安全法》和《個(gè)人信息保護(hù)法》,也都未明確個(gè)人信息的歸屬權(quán)。法律的缺位,造成了個(gè)人數(shù)據(jù)確權(quán)的模糊。
20 世紀(jì) 30 年代,由于攝影技術(shù)的進(jìn)步,新聞業(yè)開始在報(bào)紙中大量使用照片。但這些照片往往未經(jīng)個(gè)人同意。
1980 年,律師薩繆爾·沃倫(Samuel D. Warren)和路易斯·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就這個(gè)問題在《哈佛法學(xué)評(píng)論》發(fā)表文章《隱私權(quán)》,這是法學(xué)界首次提出了隱私權(quán)的概念。
沃倫和布蘭戴斯發(fā)表在《哈佛法學(xué)評(píng)論》上的文章:《隱私權(quán)》|圖片來源:布蘭戴斯大學(xué)
技術(shù)的擴(kuò)張侵犯了個(gè)人的邊界,從一開始,技術(shù)就與隱私相伴而生。
在眼下數(shù)據(jù)流通越來越嚴(yán)格,而數(shù)據(jù)紅利將盡的情況下,包括谷歌、英特爾、微眾銀行在內(nèi)的許多公司都在開發(fā)一種叫做聯(lián)邦學(xué)習(xí)或者共享學(xué)習(xí)的技術(shù)。
由于數(shù)據(jù)合規(guī)或者商業(yè)競爭的關(guān)系,許多數(shù)據(jù)在行業(yè)甚至公司內(nèi)部都無法流通,這就是公司們頭疼的「數(shù)據(jù)孤島」問題。
聯(lián)邦學(xué)習(xí)是隱私計(jì)算的一種。在手機(jī)上訓(xùn)練模型后,它只將模型加密上傳,而把用戶的數(shù)據(jù)留在了本地。
微眾銀行的首席 AI 官楊強(qiáng)曾經(jīng)把這個(gè)模型比作是「羊」,而數(shù)據(jù)就是「草料」。
過去訓(xùn)練模型的做法是從各個(gè)草場運(yùn)草過來喂羊。但是在運(yùn)送過程中,草有丟失的風(fēng)險(xiǎn),這就是數(shù)據(jù)泄漏。
聯(lián)邦學(xué)習(xí)的做法是,讓這頭「羊」走起來,到各個(gè)草場自己吃草。這樣,草就永遠(yuǎn)只留在本地,也就沒有了丟失的風(fēng)險(xiǎn)。
主人不知道羊吃了哪些草,但羊依舊長大了|圖片來源:微眾銀行
其實(shí)把模型訓(xùn)練比作「耕牛」可能更好理解,這些耕牛原來是吃八方來的數(shù)據(jù)草料,變得強(qiáng)壯后再成為企業(yè)服務(wù)客戶的「生產(chǎn)力」。而現(xiàn)在是把「耕牛」送到用戶的田地里,吃用戶數(shù)據(jù)草料,也直接更好地服務(wù)用戶。加上「數(shù)據(jù)模型的集體升級(jí)能力」,這讓你家的牛也和其他的牛可以一起成長,更好地服務(wù)你。
顯然,通過技術(shù)模式的進(jìn)步,才可以根本上避免數(shù)據(jù)泄露和惡意使用。對(duì)于日趨白熱化的數(shù)據(jù)爭奪而言,有了這種根本性的改變,才可以讓公司間的數(shù)據(jù)共享成為可能。而在技術(shù)上建立一套數(shù)據(jù)保護(hù)的制度,也才能贏得用戶的信任。
說到底,沒有任何的公司,可以依靠價(jià)值觀來成為個(gè)人數(shù)據(jù)問題的救世主。這些由技術(shù)帶來的問題,最終還是需要由技術(shù)來解決它。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hào) “極客公園”(ID:geekpark),作者:湯一濤,36氪經(jīng)授權(quán)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