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門外漢打造的“歐洲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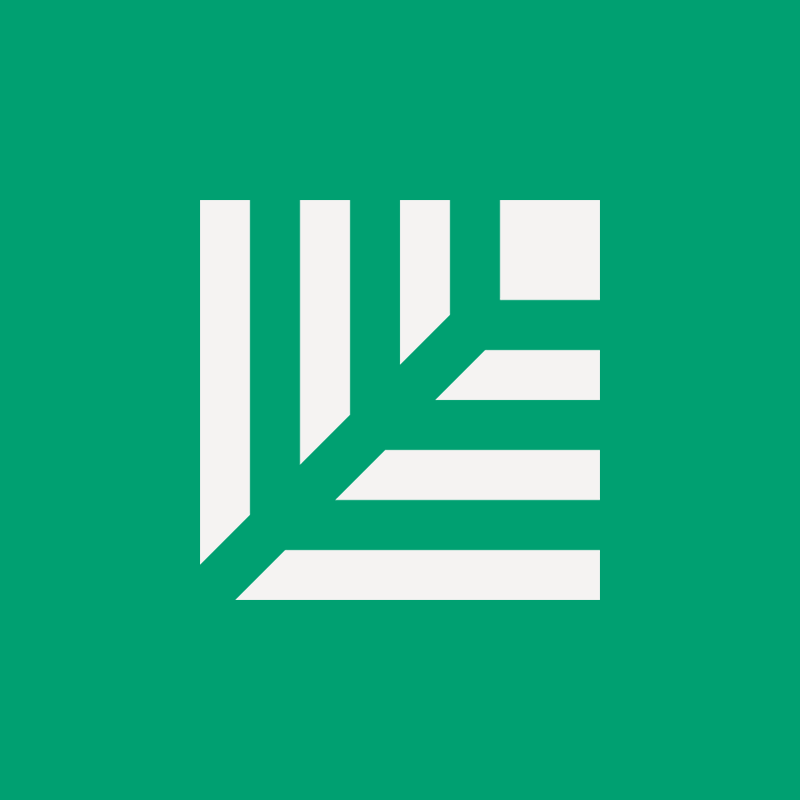
你能想象嗎?一度被稱為歐洲最大的金融科技獨角獸公司Klarna,其實是由一個“門外漢”創立的。Sebastian Siemiatkowski是一個不典型的科技創業者:他從事過一大堆零工,最喜歡的是電話推銷工作,讀了商學院入學兩年就請假去“尋找自我”,從漢堡王的兼職中得到創業的啟發,大膽而又十分情緒化,甚至還有些自大……不過,也正是這些經歷與性格,讓Sebastian盡管經歷著各種動蕩,但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會努力扭轉企業艱難的局勢。
初創企業往往容易掉進只顧埋頭奮進的怪圈,但想要獲得更好的發展,你必須時不時停下來反思一些重要且關鍵的難題。比如我們現在這樣做事是最有效率的嗎?有沒有方法可以讓我們更專注地完成這個目標?公司的成敗有時就取決于你怎么回答。
——Klarna聯合創始人兼CEO
Sebastian Siemiatkowski
幾乎沒有科技行業的創業者會說自己創業是受了快餐業的啟發,但瑞典金融科技公司Klarna的聯合創始人兼CEO Sebastian Siemiatkowski是例外。十幾歲時在漢堡王的打工經歷,讓他看到了這家快餐巨頭許多值得欽佩的地方。
“這些速食連鎖店的流程細致得令人驚嘆。”Sebastian興奮地說道,“盡管它們沒有像軟件公司那樣的技術優勢,靠的只是薄利多銷,生意還常常受人擠壓,但我是自己創業多年之后才明白,它們的系統設計得多么完美。”
在漢堡王工作的兩年不僅讓Sebastian切身體會到了良好運轉機制對企業的重要性,也讓他結識了一位至關重要的合作伙伴——后來和他一起創辦了Klarna的Niklas Adalberth。盡管Niklas在2015年離開了公司,但這兩位年輕人靠著在快餐店廚房結下的友誼,在經歷了一段環球之旅、一次落敗的創業比賽之后,最終于2005年促成他們共同創立了Klarna。
“Niklas像是老天給我的奇妙禮物——我年輕的時候非常自負,認定自己一定是對的。但Niklas總有辦法在我出錯時讓我意識到事情的真相。他是個非常耐心細致的人,專注且堅定;我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常常被情緒牽著鼻子走。” Sebastian說。
Sebastian把這種個性歸因于自己的移民成長經歷。父母在1980年帶著只有幾個月大的他從波蘭移民到瑞典,定居在了斯德哥爾摩郊區。當時歐洲各國間的互通程度遠不如今天,因此,即使僅相隔波羅的海的一小片海域,瑞典對于來自波蘭的他們來說仍感陌生。他們一家保留著波蘭的生活傳統,Sebastian從小在家說波蘭語,吃波蘭菜,過波蘭的天主教節日。這些經歷成為了他成長過程中的背景,縈繞不去。
父母因為移民歷經千辛,在Sebastian成長過程中,父母一直掙不到什么錢,為了基本生活苦苦掙扎。盡管父母細心周到地照顧他,但由于貧窮、父母不佳的健康狀況,他的童年并不像許多瑞典同齡人那樣無憂無慮。
不過,在艱難的日子里,Sebastian也找到了一處心靈寄托——圖書館。在圖書館中,他讀到了許多拓展想象力的好作品——包括經典的科幻小說如《銀河系指南》和Isaac Asimov(艾薩克·阿西莫夫)的作品。它們和許多諸如宜家創始人、維珍集團創始人等企業巨頭的書籍一起,培養了Sebastian通過商業改變世界的興趣。
在學校里,Sebastian是一名“全力以赴”的好學生,成績優異,思維活躍。“比如說,如果老師讓我們寫的是一份關于17世紀法國作家的小組報告,我會說服我們小組直接演一出關于莫里哀(Molière)的戲劇。”
同時,他還通過各種零工來補貼家用。除了15歲在漢堡王的工作經歷,他還做過諸如看護老年癡呆的患者、在學校教書、電話推銷互聯網訂閱服務等工作,最后這份工作讓他第一次了解到了推銷員日常的忙碌和辛苦——但他立刻愛上了這樣的工作。
“大家可能一般都不太看得上這樣的工作,但我卻覺得它很棒。”他說,“我會不斷打磨完善自己的推銷策略,直到我可以一天連續拿下16筆電話推銷的訂單,我就知道我已經把這項技藝打磨到了極致。它是一種說服的藝術,實在是非常迷人的技能。”
憑借著豐富的“職業”經歷和好學上進的好學生履歷,Sebastian最終進入了瑞典頂級學府之一的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進修商業專業。但是,在商學院的頭幾年,Sebastian感覺茫然、不開心。許多同學雄心壯志,希望畢業后進入咨詢或投資行業找份安穩工作,但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與此同時,當時全球剛經受完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沖擊,大家對于創業也沒有什么熱情。
這種現實與想象的沖突最終促使Sebastian在入學兩年后就請了假,拉上了當年在漢堡王結識的Niklas(他們之后還成為了商學院的同學),開始了一系列“自我找尋之旅”:先考了調酒學校的酒保證書;隨后去了美國佛羅里達州,想找一份游輪上的工作;最后回到了歐洲,在圣莫里茨的一個滑雪勝地當了服務員。
賺夠足夠的錢后,兩人開始計劃完成一次全程搭車的環球之旅。他們在圣莫里茨埋了一瓶香檳,作為對自己幾個月后完成旅程的獎勵。在這段旅程里,他們有一次錯過了搭上當月最后一艘從悉尼開往洛杉磯的貨船,兩人不得不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待上整整一個月,并且找到合適的工作養活自己。
這次的經歷讓他們真正明白了適應能力的重要性,而且他們也深刻體會到,辦法總比問題多——最終他們找到了廉價的宿舍床位和家具搬運工的工作。“最終我們向自己證明了,無論事情看起來多么糟糕,總能找到存活下來的辦法。”
當然,他們也趕上了時間的巧合。因為兩人曾決心整個旅程不坐飛機,雖然比原計劃晚了一個月到達北美,好在他們馬不停蹄搭便車穿越美洲大陸,最終搭船順利回到了歐洲。直到回到斯德哥爾摩,還挖出并喝光了當初埋的香檳后,他們才意識到自己差點就錯過了每年重新選課的截止日期。
“我們玩了整整一年。經過一年的旅行,我變得又瘦又窮,沒有工作,沒在上學,也沒有任何收入支撐。” Sebastian說。
回到瑞典后,Sebastian依靠福利救助和食品券過活了一段時間。隨后,他來到一家面向需要現金的小公司提供貸款、來填補應收賬款的資金空缺的保理公司當銷售員。
正是這段經歷讓他發現,許多小商家都在為支付問題發愁,特別當時正值電子商務興起,大量在線交易的收付款更是讓已經習慣線下慢交易的小商家感覺難以承受——為了保證收入現金流,不少商家要求交易只能使用借記卡現買現付。這讓Sebastian開始思考:能否有人可以作為顧客和商家的中間人,先預付貨款給商家,而在顧客收到發票時再向他們收錢呢?當時瑞典的郵購消費采用的已經是“貨到付款”的方法,那為什么電子商務世界無法像現實世界中那樣,實現“先買后付”(Buy Now Pay Later)呢?
于是在下一學期開學時,Sebastian就將這一想法告訴了Niklas和另一位同學Victor Jacobsson,他們一起創辦了一家名為Kreditor的公司,想在數字平臺上推廣“先買后付”做法。隨后,三個聯合創始人一起參加了學校的創業比賽,比賽的評委很多都是瑞典的企業精英,甚至瑞典的國王也出席了比賽。
“但很不幸,他們都不相信我們能做成。‘你們的方式根本行不通……要有這么簡單,銀行為什么自己不去推這樣的模式’……他們列舉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認為我們注定會失敗。”最終,他們在三家創業公司中排名最后。
在Sebastian看來,這次參賽受挫給他們帶來了不小的打擊,但也磨煉了意志,為將來戰勝更大的挫折做準備。“我的反應不是自暴自棄,反而是更堅定信心,說‘我會證明給你們看’。”
后來,他們通過學校里的天使投資人圈子,用公司10%的股份換取了6萬美元種子資金;隨后用這筆錢聘請了軟件工程師搭建了Kreditor平臺的第一個版本;在另一次交易中還將公司剩下股份的近2/5也置換了出去——Sebastian現在意識到,那真是個巨大的失誤。
“我們當時認為這些人會留下來幫助我們把公司建設壯大,但他們只待了一年就離開了,還帶走了他們的股份,”他說,“這是我創業的第一個教訓:你一定要在用人合同中把所有不確定性排除掉。”
但他還是靠著自己的毅力,跟聯合創始人開著老舊的沃爾沃在瑞典各地一家家地跑客戶,窮盡自己的銷售才能向小型商戶推銷先買后付的服務,最終把公司業務做了起來。他們親自上門,既給人提供一種像大銀行一樣服務成熟可靠的感覺,又堅持科技初創企業的優勢,保持形式靈活新穎。
為了獲得客戶的認真對待,他們把每個細節都打磨得無可挑剔。比如,他們特意選了一個尾數有更多0的電話號碼——在當時的瑞典,這讓人一看就覺得是大公司里有很多分機的總機號碼;他們的名片也使用了厚實的高檔紙張;他們穿上筆挺的西裝,“裝得像模像樣的”。
慢慢地,Kreditor開始獲得越來越多客戶的青睞,收入也從最開始的150萬瑞典克朗增長到了2.7億。與大部分硅谷模式下快速成長的公司不同,他們在成立后不久就實現了盈利,并多年一直保持盈利。“這意味著我們發展出了優良平衡的企業文化,為客戶創造價值才是我們獲利的真正原因,而不是簡單地追求更高的公司估值、提高品牌知名度之類。” Sebastian說。
Kreditor最早在數字領域推廣先買后付做法的先發優勢,也為公司之后幾年的擴張奠定了基礎。到了2009年,公司決定更換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提升國際知名度。Sebastian表示,換名字,只是想更好地做推廣而已,而且大家也更想維持一種創業公司的形象。
最終,“Klarna”這個名字脫穎而出——在瑞典語里有“簡單明了”的意思。Sebastian說,“我們換這個名字,是想向大家傳達一種‘支付就是這么簡單’的意思,它也是我們在金融服務行業希望達成的愿景。”
伴隨著消費者對先買后付需求的日益增長,Klarna也沒有停下發展的腳步。公司提出了新的目標:成為所有媒介與途徑數字交易的首選技術架構。在德國獲得成功后,Klarna已接近獨角獸地位,Sebastian也成為了金融技術領域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看來,是時候去征服另一個同樣正在爆炸性增長的鄰近市場了:數字支付。
Sebastian向董事會提出了他的設想并獲得了大家的一致認同。“我們分析了當時的市場格局,但我明顯有點自大而忽略了其他對手——比如當時的Stripe以及Adyen。我知道他們也在有所謀劃,我也知道我們必須時刻關注他們的動向,但我還是有點大意了。” Sebastian面帶慚愧地回憶道。
這種自大的表現之一,包括向Adyen的創始團隊提出收購邀約,但被對方拒絕。“之后,我們便決心自行建設這套支付系統。”但Sebastian承認,和Adyen最終擴張到了亞洲和其它地區的巨大市場相比,Klarna一直苦苦掙扎于在德國推出一款自己的支付產品,“這無疑是一個緩慢的期望落空的過程。”
“真正促使我們反思的關鍵時刻是2015年——Spotify選擇了與Adyen合作,而不是我們。”
這一令人沮喪的失敗最終成為了Klarna的重要轉折點。當時在Sebastian面前有兩個選擇:要么賣掉公司、退出競爭;要么加倍下注Klarna的核心競爭力,讓先買后付更深地嵌入整個歐洲的消費金融領域,同時去發展最大的目標市場:美國。他選擇了后者——但在此之前,他先對公司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變革。
Sebastian 嘗試了各種可能的辦法來重塑Klarna的企業文化。“比如像谷歌那樣,允許員工將自己20%的工作時間用于個人項目,在娛樂室里放了樂高玩具和乒乓球桌,但最終沒有任何改變。”
之所以采取這些方式,是為了解決讓員工做事無法靈活變通的根本問題,但后來Sebastian才發現,問題出現在Klarna的組織構架上,它限制了大家實現愿景的能力。
這其實也是困擾著無數想要找尋新方向的公司的難題:組織架構限制了技術和業務部門之間的互通,以至于兩大部門各自為政;夾在兩個部門中間的是產品部,它本該是另兩個部門的橋梁,結果只是分別成為了兩個垂直部門的配合部門。這種組織構架導致的結果就是——出了問題就會彼此推脫,最后就變成了無休無止、毫無意義的互相指責。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Sebastian和他的團隊再次向硅谷取經,但比起之前相對淺表的變革,這次則是要動真格——對公司的整體架構進行全面的重組。
“像亞馬遜這樣的公司,基本上是由一個個小型的跨職能團隊組成的,各團隊會以全局的眼光解決一個個的問題。他們有一頁紙就能放下的使命宣言,然后大家就遵照其指引,調動公司的資源去達成這些使命。正是在復盤他們的做法的過程中,我們才意識到,Klarna也需要變成這樣的架構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重組很快就產生了積極影響。“大家做事的動力變得更足,并且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正向氛圍,產品推陳出新的速度變得更快,功能更新迭代也更迅速。當然,我們也知道,改變無法一蹴而就,需要時間和耐心,有些員工一開始也并不相信能帶來什么真的改變,但從長遠來講,公司必定是能從中受益的。”
這一轉變也為Klarna進入美國市場創造了條件。2015年,他們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還有紐約市開設了辦事處,著手一些基礎的準備工作;到2018年時,他們開始大力推進。Sebastian采用了和初期類似的做法,日程表里滿是與各個精心挑選的潛在客戶會面的安排——而爭取這些客戶,則是為了超越其當時在先買后付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來自澳大利亞的Afterpay。
“我們知道Afterpay當時領先于我們,但我們并不氣餒灰心,而是齊心協力加入這場競爭并努力取勝。”
再后來,突然爆發的新冠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節奏,Klarna也只能先停下腳步觀望。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Klarna在2019時在美國上線了直面消費者的應用程序,在此期間,用戶量開始爆發式增長。
盡管后來又經歷了各種動蕩,但Sebastian覺得,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要努力做各種艱難抉擇,來扭轉局勢。
“隨著年齡增長,你會開始更能掌控這些創業過程中的起起伏伏。”他說,“初創企業往往容易掉進只顧埋頭奮進的怪圈,但想要獲得更好的發展,你必須時不時停下來反思一些重要且關鍵的難題。比如我們現在這樣做事是最有效率的嗎?有沒有方法可以讓我們更專注地完成這個目標?公司的成敗有時就取決于你怎么回答。我們當時的處境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價值近數千億美元的行業中,Klarna終于站穩了腳根,而且占據著重要地位。盡管如今Sebastian的成就已經遠超大家的想象,但他身上不想辜負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后代,他的股東和員工、顧客以及更廣闊的世界等)的那股勁頭,至今仍在他的個人和職業故事中若隱若現,成為一切的底色。對于很多人來說,這樣的責任心可能難以承受,但對Sebastian來說,則是他不斷前進的動力源泉。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紅杉匯”(ID:Sequoiacap),作者:洪杉,36氪經授權發布。











